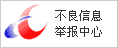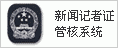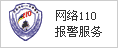眾所周知,“創(chuàng)意寫作”起源于美國,發(fā)展于英語國家,至今已有百余年歷史,現(xiàn)已成為一種具有世界影響的非常重要的高校人才培養(yǎng)模式,而且在英語國家已由高校蔓延到中小學,形成了創(chuàng)造性人才培養(yǎng)的一種比較成熟的教育體系。2009年,復(fù)旦大學獲批成立國內(nèi)創(chuàng)意寫作專業(yè)碩士MFA學位,上海大學中國創(chuàng)意寫作中心成立,創(chuàng)意寫作在中國正式落地生根。經(jīng)過十多年的快速發(fā)展,中國創(chuàng)意寫作已經(jīng)從引入、模仿的初級階段,進入到中國化探索與“中國學派”建構(gòu)的高級階段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在創(chuàng)意寫作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,上海大學功不可沒,在葛紅兵、許道軍、譚旭東、張永祿、謝尚發(fā)等諸位學者的不懈努力下,不僅系統(tǒng)譯介引進了英語國家創(chuàng)意寫作理論與實踐著作,還全身心地投入到創(chuàng)意寫作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(shè)、人才培養(yǎng)、教材編寫、教師培訓、活動組織,包括此次升級版的“中國創(chuàng)意寫作研究院”揭牌,可以說形成了獨具特色、影響深遠的創(chuàng)意寫作“上大模式”,引領(lǐng)和帶動了國內(nèi)其他高校和眾多中青年學者積極投身創(chuàng)意寫作事業(yè),為中國創(chuàng)意寫作的發(fā)展、完善以及融入世界作出了重要貢獻。
總體來看,我認為,中國創(chuàng)意寫作基本形成了以文學教育、文化產(chǎn)業(yè)和文化創(chuàng)新為核心的中國式發(fā)展路徑,構(gòu)建起以本體論研究和方法論研究相結(jié)合、理論研究與教育實踐相同步的中國式“創(chuàng)意寫作學”,形成了以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為主要依托的中國式學科建設(shè)模式,以“創(chuàng)意寫作”課教學為主的中國式課程教學模式,以培養(yǎng)專業(yè)本科、碩士和學術(shù)碩士、博士等創(chuàng)新人才為目標的中國式專業(yè)教育模式。顯而易見,中國創(chuàng)意寫作不同于英美創(chuàng)意寫作,是具有世界眼光和中國特色的創(chuàng)意寫作,其學術(shù)意義在于,不僅在中國化、全球化的雙重語境中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,而且已經(jīng)走出孤軍奮戰(zhàn)的局面,日益融入中國當代文學、文化生產(chǎn)的整體機制和未來圖景中,尤其是葛老師提出的“創(chuàng)意本位的新文科”,為當下新文科建設(shè)提供了一種可能性;其教育意義在于,一定程度上改革了自足、僵化、與就業(yè)市場脫節(jié)的傳統(tǒng)中文教育和文學教育,初步提出了意在發(fā)揮創(chuàng)意寫作通識教育功能的“通識本位的創(chuàng)意寫作”,通過跨學科、跨專業(yè)的教育模式,通過師生共創(chuàng)的工坊式課堂教學模式,培養(yǎng)了一批具有創(chuàng)造性思維的能夠適應(yīng)新時代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發(fā)展所需的復(fù)合型人才,為中國現(xiàn)代教育的完善提供了一種方案。
下面再來說說創(chuàng)意寫作的“現(xiàn)代化”。我們知道,整個1980年代都在談?wù)?ldquo;現(xiàn)代化”,比如建設(shè)“四個現(xiàn)代化”,但人們談?wù)?ldquo;現(xiàn)代化”的方式就好像這是一種不言自明、自然而然的事實,一套不需要追問其來源的普泛的價值標準。也就是說,它被視為一種“天經(jīng)地義”的信仰和價值觀,而并不被作為一種“理論”,更不被看作一種應(yīng)當被歷史化并接受批判性質(zhì)疑的話語對象。事實上,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,“這不過是西方中心國(尤其是美國)為確立霸權(quán)地位,而從西方社會發(fā)展中提取思想資源和合法性依據(jù),并由其國家的社會科學知識精英‘發(fā)明’的一套歷史敘述”(賀桂梅《“新啟蒙”知識檔案——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》)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我們今天提出“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”不僅僅是對四十年來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實踐經(jīng)驗的理論總結(jié),也是對美國式現(xiàn)代化理論的批判性質(zhì)疑和反思,換句話說,“現(xiàn)代化”是復(fù)數(shù)的而不是單數(shù)的,“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”確實有必要取代新時期以來的“現(xiàn)代化”想象而成為直面當下和迎向未來的一種國家意識形態(tài)。
毋庸諱言,與當今中國所取得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等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建設(shè)成就相比,中國創(chuàng)意寫作盡管已經(jīng)初步實現(xiàn)了“中國式”,但離真正的“現(xiàn)代化”顯然還有一定的距離,還存在著諸多問題。比如,盡管已形成了相對成熟的“復(fù)旦模式”“上大模式”“北師大模式”,但絕大部分高校的創(chuàng)意寫作尚未形成像加拿大高校那樣的“全方位的支持體系”,依然處于散兵游勇狀態(tài);在現(xiàn)有的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體系下,創(chuàng)意寫作的生存和發(fā)展受到一定的制約,即使北京大學中文系也會因為師資和課程的缺乏而取消創(chuàng)意寫作專業(yè)碩士的招生;目前全國雖然有700余所高校開設(shè)了創(chuàng)意寫作課程,但還有3/4的高校(包括筆者所在的地方高校)依然沒有創(chuàng)意寫作專業(yè),依然延續(xù)著傳統(tǒng)的基礎(chǔ)寫作課程教學;如此等等。
因此,要真正實現(xiàn)中國創(chuàng)意寫作的現(xiàn)代化,我認為還需要更努力地做到“六個堅決打破”:一是堅決打破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壁壘,繼續(xù)引進和借鑒國外的理論經(jīng)驗與教育方法,繼續(xù)立足本土語境,建構(gòu)創(chuàng)意寫作的中國學派;二是堅決打破中文學科壁壘,持續(xù)推進新文科建設(shè),從中文學科走向跨學科和交叉學科;三是堅決打破學院之間的壁壘,重組課程體系和人才培養(yǎng)方案,從文學教育走向通識教育,實現(xiàn)校內(nèi)外資源的重新整合和優(yōu)化配置;四是堅決打破大學與社會之間的壁壘,讓更多作家、藝術(shù)家、美學家、創(chuàng)意師等進入大學,從文學創(chuàng)意走向文化藝術(shù)創(chuàng)意,大力發(fā)展與市場緊密接軌的文化藝術(shù)創(chuàng)意產(chǎn)業(yè);五是堅決打破高等教育與基礎(chǔ)教育的之間的壁壘,從大學創(chuàng)意寫作走向中小學創(chuàng)意寫作,逐步形成全方位一體化的專業(yè)教育體系;六是堅決打破舊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壁壘,實現(xiàn)人文主義的“創(chuàng)意”與技術(shù)主義的“媒介”的共生互動,培養(yǎng)學生成為具有復(fù)合型知識體系、具備新媒體行業(yè)寫作能力和從業(yè)要求的創(chuàng)造者;如此等等。
總之,在人工智能高速發(fā)展的新時代,我們要通過學科體系、學術(shù)體系、話語體系以及專業(yè)課程體系與人才培養(yǎng)體系等建設(shè),力爭早日實現(xiàn)創(chuàng)意寫作的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。
來源:光明網(wǎng)